
大家印象中的陶淵明非常清寒。但其實他的家世背景非常雄厚。陶淵明的曾祖父是晉朝名將「陶侃」,最輝煌時,官位相當於現今的國防部部長;但到了陶淵明這一代,因為陶侃後繼無人,又被政敵庾亮清算,所以家產也差不多都沒了。不過憑著陶氏家族的餘燼,還是能幫陶淵明找到一些不錯的官位。
明明起跑點就比別人超前許多的陶淵明,究竟怎麼會落到「清貧」的下場?在《讀懂古人的痛,就能跳過現代的坑》這本書中,作者林俐君(綠君麻麻)就給了大家一個答案。
古代最具代表性的「躺平族」、「草莓族」
陶淵明家世驚人,雖然家產幾乎沒了,但官場上還是有不少人脈,依舊能不廢吹灰之力得到許多輕鬆的官位。據《晉書》記載:「以親老家貧,起為州祭酒。」陶淵明一當官就有類似於縣市教育局局長的要職,但是陶淵明不喜歡,他說:「不堪吏職,少日自解歸。」(工作實在太累了,上班幾天就自己辭職了)
後來還有幾次不錯的工作機會,也都隨便做做就不做了,放到現在來看,就是個草莓族、躺平族。最後真的窮到不行了,就跑去問叔叔:「聊欲弦歌,以為三徑之資可乎?」(有沒有那種不太累,能讓我每天喝喝酒、唱唱歌的工作?)叔叔馬上幫他走後門弄到一個小官,於是陶淵明成了彭澤縣令。
本以為這樣就天下太平,做個地方小官不太累,應該不會隨便辭職吧!結果上班沒幾天,長官要來視察,旁人勸他見長官時候要穿正式一點(可能平常都穿吊嘎跟拖鞋辦公),陶淵明就爆氣了,說出了那句名言:「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,拳拳事鄉里小人邪!」意思是,他沒辦法只為了這一丁點的薪水,對這些粗鄙的小人鞠躬哈腰,便又辭職了。
看到這邊,各位的拳頭是不是有點硬硬der?你陶淵明的腰到底是有多硬?要給你多少錢才會掰彎?好啊既然你嫌五斗米少,我們就來看看五斗米折合臺幣到底是多少?

「五斗米」折合臺幣多少錢?
以下引用數感實驗室 Numeracy Lab的資料:陶淵明所處的時代為東晉,當時的俸祿為「半錢半穀制」,也就是薪水當中有一半是錢財,另一半則是米糧。以陶淵明所任的縣令來看,俸祿為「月錢二千五百,米十五斛」。
若單純只看米的部分,一個月可拿到十五斛,相當於一百五十斗,換算下來一天就是五斗米。啊!原來陶淵明不甘願折腰的五斗米指的是他的日薪,但陶淵明你不是打零工的耶!當到地方父母官了,至少要用月薪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薪水吧!
延伸閱讀:蘇軾若活在現代,恐跟國師唐綺陽當好友!愛講「呵呵」還超迷星座【沙發讀書】
古代薪酬怎麼換算?
我們假設「兩千五百銀兩」跟「十五斛的米」價值相等,把俸祿銀兩全換成米來計算,那麼陶淵明相當於一個月領有三百斗米。把魏晉南北朝與現代的體積、重量單位換算,就可得知:
150斗×2=300斗(一個月的米)=3000升(魏晉南北朝)= 613,500毫升(現代)
613,500毫升 × 0.85 g/毫升(粳米密度 )= 521,475公克 = 521.475 公斤 =7000多碗飯
若陶淵明孤家寡人、一人飽全家飽,一天吃三碗飯的話,陶淵明一個月拿到的米糧,可以吃6.5年。陶淵明真的不考慮忍氣吞聲嗎?
陶淵明的月薪,換算台幣有多少?
陶淵明的薪水來自經濟作物,可能因為物價波動時高時低,同時也讓人好奇,這麼多的米到底值多少錢呢?對照農糧署於2022年九月公布的粳米價格,為每公斤45.46元,得出陶淵明的月薪價值相當23,706元。
但跟中國古代相比,現代的農業技術更為發達進步,再加上科技的推動,讓農業收穫成本大幅降低;所以現在的米價應該比古代來得便宜許多,若粗略地把米價放大八至十倍,那麼陶淵明的月薪應該是18萬至20萬,跟當今的縣(市)長就相當接近了。
天啊,一個月近二十萬耶,不要是說折腰了,我還能劈腿呢!陶淵明你咖骨就不能軟Q一點嗎?你的五個廢柴兒子還要補習呢!

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
其實從陶淵明三次做官又三次辭官和他寫的詩,可以清楚看出,他一直在是否做官的問題上掙扎。陶淵明的家世赫赫有名,照道理說,做官是最好也最自然的選擇,既有豐厚的俸祿,也有亮麗的人脈。然而,在東晉末年的環境下,戰亂不斷,想要能安穩地做官,不僅要有柔軟的身段,也要有機詐狡猾的心機,才能在複雜的官場上生存下來。
陶淵明並不喜歡(當然也不善於)混這個圈子,他更喜歡清靜,喝喝酒、寫寫詩、種種地、逗逗孩子,寫下「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」這樣的文字時,便可以感受到一種真正來自他靈魂深處的自由與舒展。所以,與其說他拒絕了高官厚祿,當了草莓族、躺平族,倒不如說他追求的是心靈及精神層面的價值。
蘇軾曾這樣評價陶淵明:「欲仕則仕,不以求之為嫌;欲隱則隱,不以去之為高。 飢則扣門而乞食;飽則雞黍以迎客。 古今賢之,貴其真也。」(想要做官,那就去追求,不要因為追求仕途而感到不好意思;想要歸隱山林,那就去歸隱,也不要以為歸隱就顯得清高。饑餓就敲門乞討食物,飽了就殺雞宴請賓客。古今往來的閒人智者,他們的誠貴之處在於其本性率真。)
陶淵明的可貴之處,就在於他的真,以及放得下和看得透,真正活出快樂。許多人一邊過著不喜歡的生活,一邊抱怨,又何嘗能真正地活著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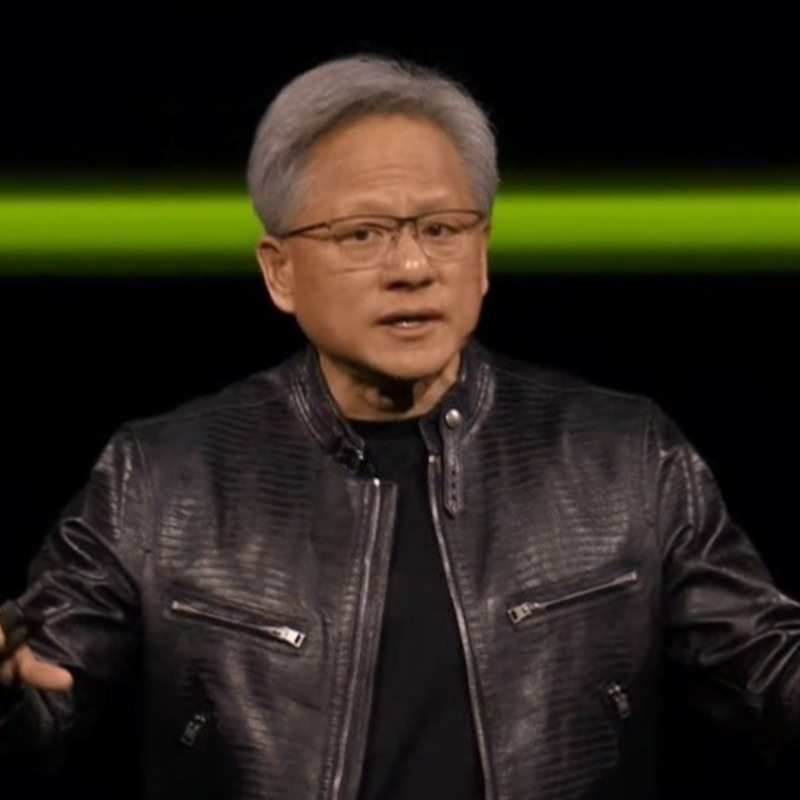

.png)


















